城市消耗了80%以上的能源和碳排放,未来城市形态怎么发展,将为蓝天和低碳的协同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未来城市建设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刘艳美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 图片来源: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主办方提供
今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意味着,我们只有30年时间完成数值下降,而欧盟是5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说,“所以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10月24日,贺克斌继一周前参加2020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后,又马不停蹄出现在成都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会场。他再度指出,“未来两个五年规划将非常关键,如果2030年峰值爬得太高,后面碳中和的目标就会很难实现。”
据他透露,最新动向是,全国层面正在研究编制一项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比照当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十条”,将针对各个部门和地域制定细分任务,也将包含一些可核查可考察的内容。
“我国是全球传统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之后可能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关键是抓技术先机问题。如果按传统发展模式也能扛一段时间,但这样一来技术全部接不上,可能扛到最后突然来个突变吗?这肯定不是我们应做的选择,因此,中间一定要有衔接,并且要及早布局。”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张人禾指出,回顾过去我国制定的阶段性大气治理目标,基本上都在计划时间逐一达标。
体现在数据上,贺克斌展示了一张综合显示GDP、机动车年均行驶里程、人口等经济发展指标和大气污染物减少指标的折线图。2013年开始,随着上侧经济发展指标继续上升同时,污染物指标开始明显下降,呈现出一种“喇叭图”的形状。这表明,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已然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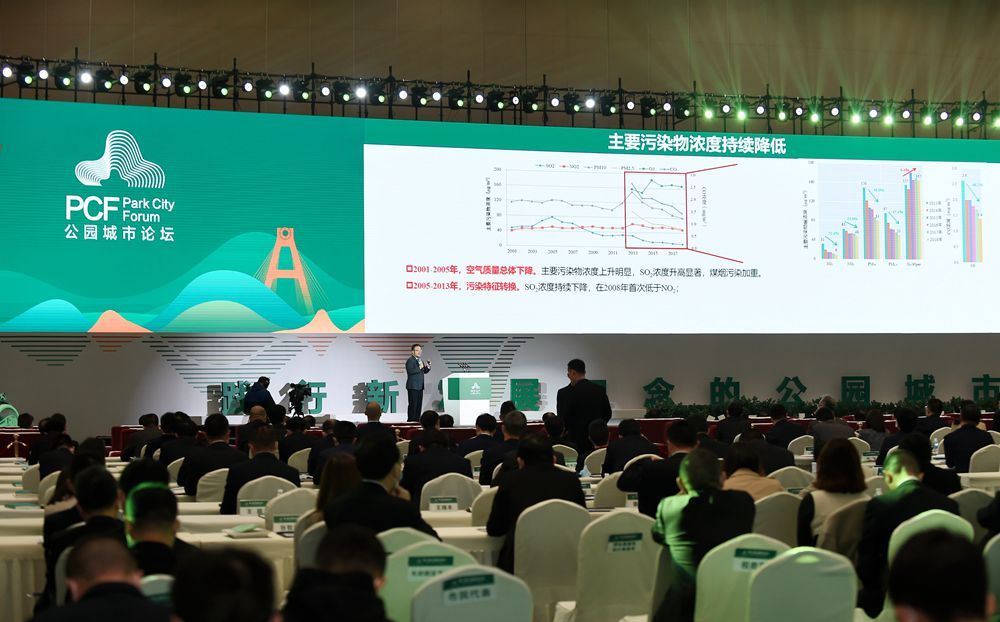
图片来源: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主办方提供
如今,不同污染物排放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需求。
据贺克斌展示的统计数据,自1990年至2019年,全国各类大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的排放在2006年就出现最早的拐点,降幅到现在已超过80%;PM2.5一次排放量在2005年开始下降,接下来是2012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但同时,VOCs(易挥发有机物)、臭氧和二氧化碳排放则构成新的治理难点。
面对接下来“十四五”时期大气治理的新特点,贺克斌提倡一种系统性的治理方案。
比如,针对臭氧的减排难题,他研究发现,需要同时考虑氮氧化物和VOCs的减排情况。氮氧化物和VOCs的排放比例将影响臭氧排放,因此要进一步完成减排,协同共治势在必行。
而在减碳问题上,更多因素将被纳入考虑当中。
根据一项针对中国低碳发展的战略研究,若要在2050年实现碳排放基本接近于零,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将可能同时对环境带来极大利好,实现70%~90%常规污染物减排,并使氮氧化物、VOCs和PM2.5排放量与二氧化硫一道降至百万级别。大幅度能源结构调整和碳排放协同值得期待,但同时,亦需要警惕高强度政策对经济社会很强的反作用力。
贺克斌认为,这也要求许多工作在“十四五”期间及早布局。
“现在已经有电厂可以做到常规污染物超低排放,不引入碳的因素,对增加污染物影响并不大。但电厂这样的基础设施通常有40年寿命,并造成锁定效应。若要考虑碳中和问题,若仍以这种方式发展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贺克斌分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以50年为周期,长短结合来分析问题。”
这也意味着,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将在短期内发生。
据贺克斌介绍,一些新出现的情况有望缓和部分矛盾。比如,最近十余年风能、太阳能成本下降,为化石燃料转型带来机遇,而在备受关注的就业岗位问题上,有统计显示,当新能源产业真正实现发展后,其提供的就业将是传统能源产业2~3倍。
在他看来,许多矛盾还将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因此,抢占技术发展先机将格外重要。以禁售燃油车为例,欧洲国家已经列出30~40年时间表,中国也摆在研究议事日程上,但早做打算,将更有机会争取技术发展的窗口期。
而若将减排任务细化到每一个区域,城市将是重中之重。如贺克斌所说,城市消耗了80%以上的能源和碳排放,未来城市形态怎么发展,将为蓝天和低碳的协同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未来城市建设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而他也指出,最近在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公园城市”理念,将有望推动城市从结构上满足减排要求。
“环境质量是工业城市的一个底色,想要打好底色,公园城市的理念就能够用来推进未来城市的发展。”贺克斌解释,“在此理念下,它已经不是单纯从环保部门来抓底色问题,而是从一个综合发展的包括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角度来抓底色问题。”
他提到正在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成都。“最近几年间,特别是在建设公园城市推动下,成都的空气治理水平基本上跟上了东部地区的节奏,改善幅度非常明显。而考虑到盆地气象条件,成都面临的困难还更多。因此,从效果来看,成都做了很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他指出。
“示范”则说明,成都需要从公园城市角度出发,探索更多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有效经验。
在此前参加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时,贺克斌就曾强调平台的作用。他认为,在结构问题难解、各种涉及零碳与负碳的新技术有需要加速上马的当下,需要将研发、制造、市场、金融等多个环节和要素资源更多加以整合,更快找准方向,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更重要的是,眼前的问题也需要有城市充当先行者,为下一步发展破冰。
“在‘十四五’乃至今后,到了要动结构才能实现更多减排量的时期,‘伸手能摘到的苹果’已经摘得差不多了,往后可能要‘搭个梯子’才能摘,甚至要‘放个猴’帮你摘。改善的幅度在一点点收窄,难度越来越大,也更需要城市下决心,久久为功。在公园城市理念和实践推动下,成都应该比别的城市更快达成共识,走上协同的道路。”贺克斌指出。
他也发现,一些新的业态释放出更多有利信号。“比如成都布局的节能减排产业、信息产业以及通用航空产业等,它们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也发挥了本土产业优势。”他认为,通过对新产业的强调,公园城市将能够为中长期发展打下良好结构性基础。

1本文为《每日经济新闻》原创作品。
2 未经《每日经济新闻》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等,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