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3日,第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徐飞博士强调,在算法主导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经典阅读。AGI技术使知识传播模式发生变革,导致人类认知出现碎片化、单向度化、意义空心化等困境。而经典作品蕴含的人类思维精华、情感深度与价值判断,能抵御技术异化。徐飞博士呼吁人们重视经典阅读,在技术狂飙中锚定精神坐标,守护人性尊严,走向更具尊严的未来。
每经编辑|唐元
在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逐渐包裹全球,当生成式AI开始批量生产文本,当知识获取变得如点击屏幕般轻而易举,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
2025年4月23日,我们迎来第30个“世界读书日”。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哈佛大学、MIT高级访问学者徐飞博士认为,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经典阅读。经典作品所蕴含的人类思维精华、情感深度与价值判断,构成了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堡垒。本质上,重视经典阅读是人类在技术狂飙中锚定精神坐标的自觉努力。

(一)技术重构下的阅读生态异化
在AGI构建的数字生态中,知识传播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根据2024年《全球数字阅读报告》,人类日均接触电子屏幕时间已达6.2小时,其中78%的信息获取依赖算法推荐。这种“投喂式”阅读导致认知出现三重异化:首先,是注意力的碎片化。社交媒体的15秒视频培养出“滑动拇指的一代”,深度阅读能力以每年12%的速度衰退(MIT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数据)。神经科学家发现,频繁切换信息源会导致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突触连接密度下降,使人类逐渐丧失聚焦复杂议题的能力。
其次,是思维的单向度化。算法通过“协同过滤”不断强化既有认知,使波普尔所言的“猜想与反驳”的科学精神沦为数据茧房中的自我循环。社交媒体平台的“回声室效应”让用户陷入认知闭环,2023年剑桥大学研究显示,长期使用推荐算法的用户,其观点多样性较十年前下降47%。
第三,是意义的空心化。海量信息如洪水般冲刷着精神世界,却难以沉淀为托克维尔笔下“心灵的习惯”。当短视频平台日均产生1.2亿条碎片化内容,人类的精神世界正面临着鲍德里亚所说的“信息透明性暴力”,过剩的信息反而导致意义生产机制的瘫痪。
这种困境在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文传统的挑战。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警示的文字遗忘危险,在算法时代获得了新的注脚:当AI可以瞬间生成《哈姆雷特》的情节摘要,当GPT-5能模仿但丁的笔触创作十四行诗,人类正在失去与经典文本对话的耐心。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强调的“视域融合”阅读过程,被简化为数据输入输出的机械过程。以语言模型为例,其对文本的处理基于统计概率而非意义理解,这种“模式识别”式的认知方式,消解了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作者意图与读者反思形成的意义网络。在二进制代码的切割下,《论语》的“仁”沦为词频统计中的高频词汇,《神曲》的救赎主题被拆解为情感分析模型中的正向数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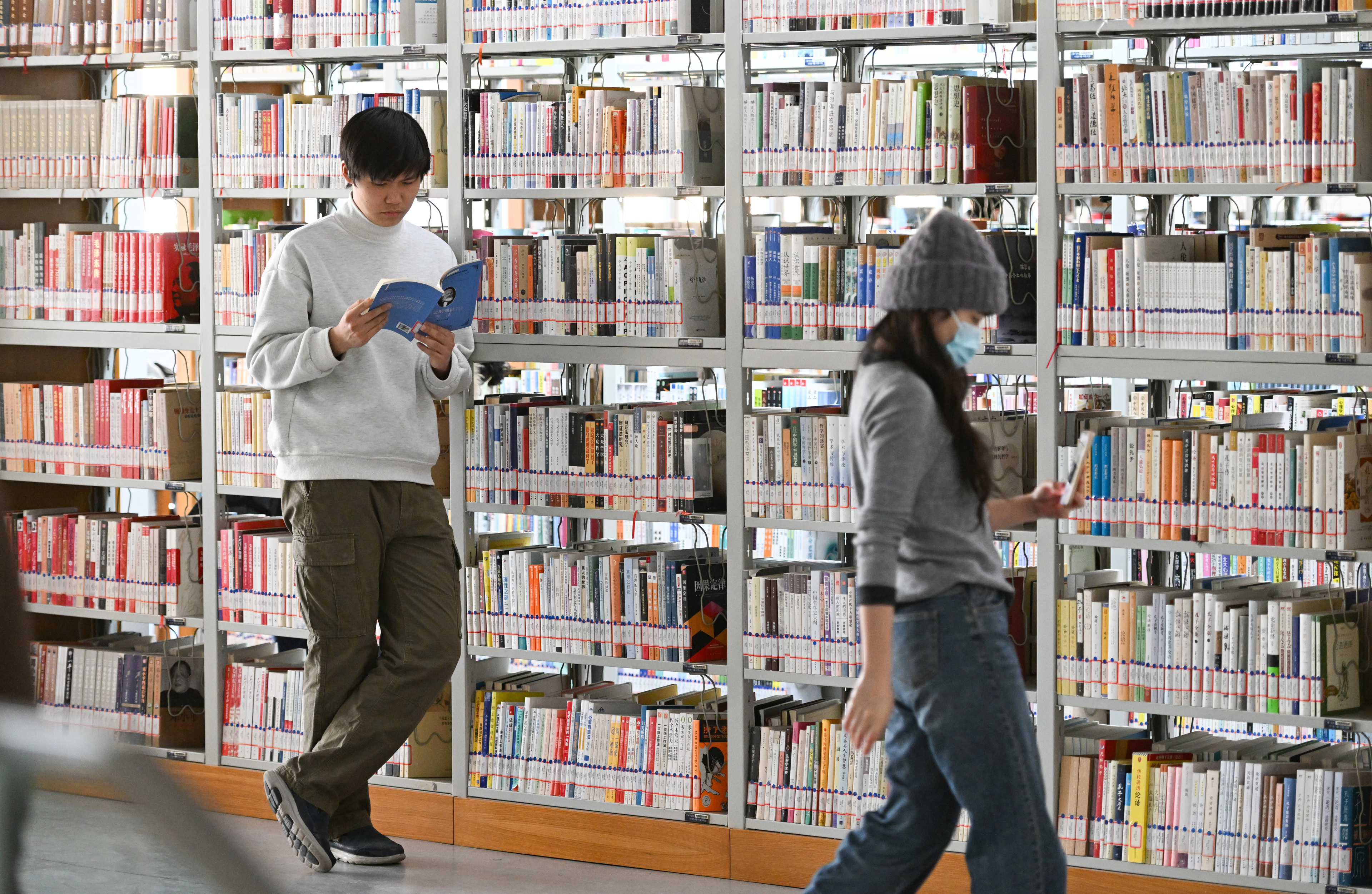
(二)生成式AI对认知主体性的消解
随着AGI技术的发展,生成式AI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的范式。OpenAI的GPT系列模型已能生成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甚至哲学论述,这种“技术模仿”带来的认知危机远超工业革命时期的体力替代。
2024年《自然》杂志的实验显示,83%的大学生无法准确区分AI生成的哲学论文与人类学者的作品。当知识生产变得触手可及,康德所言的“理性自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不再需要通过艰苦的思考来建构认知,而是依赖算法直接获取“答案”。这种认知惰性的蔓延,正在摧毁苏格拉底“产婆术”所代表的批判性思维传统,使知识获取沦为被动的信息接收。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价值判断体系的崩塌。算法推荐的核心逻辑是用户偏好的最大化满足,这导致鲍曼所说的“液态现代性”在认知领域的具象化:一切价值判断被简化为点击量、点赞数构成的量化指标,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永恒命题——如真、善、美——在流量逻辑下被边缘化。当某平台《存在与时间》的推荐量不及娱乐八卦的1/200,当《庄子》的哲学思想被转化为短视频平台的“人生智慧”片段,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扁平化革命。
(一)经典作为时间筛子的选择机制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其经过时间维度的残酷筛选。艾柯在《开放的作品》中提出,经典文本具有“开放性结构”,每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新的意义。以《论语》为例,朱熹从中读出“格物致知”,王阳明看到“知行合一”,当代学者则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中,找到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启示。这种跨时空的对话能力,正是经典抵御算法同质化的核心优势——当AI根据用户画像推送定制化内容时,经典文本却在不断打破既有认知,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般催生新的思考。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强调,经典的价值在于其“陌生性”,即每次阅读都能带来未被发掘的意义,这种永无止境的阐释空间,与算法推荐的“信息适配”形成根本对立。
从文明传承的角度看,经典文本构成了人类精神的“基因库”。中国的《诗经》保存了先秦时期的文化密码,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承载着英雄时代的价值体系,印度的《奥义书》记录了古印度哲学的思辨轨迹。这些跨越千年的文本,如同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言的“文化灵魂”,是不同文明应对生存挑战的智慧结晶。当AGI试图用数据模型模拟人类文明,经典文本的不可还原性成为技术理性的边界——你可以用算法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关系网络,却无法复制黛玉葬花时那种对生命本质的诗意凝视。
(二)深度阅读对认知能力的锻造
经典阅读培养的是一种反算法的深度认知模式。神经科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在《普鲁斯特与乌贼》中揭示,阅读复杂文本时,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激活,促进抽象思维与共情能力的协同发展。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阅读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时,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产生类似真实社交的神经活动,这种“认知共情”能力在碎片化阅读中会显著退化。
当我们沉浸于《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里茨战场的星空下的顿悟,或是《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时的生命沉思,这种超越功利的精神体验,正在重塑被短视频碎片化的大脑神经回路。正如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强调的,真正的教育始于对经典的“批判性占有”,这种占有不是知识的囤积,而是心智的锻造——它教会我们在信息的汪洋中辨别珍珠与砂砾,在观点的喧嚣中坚守思考的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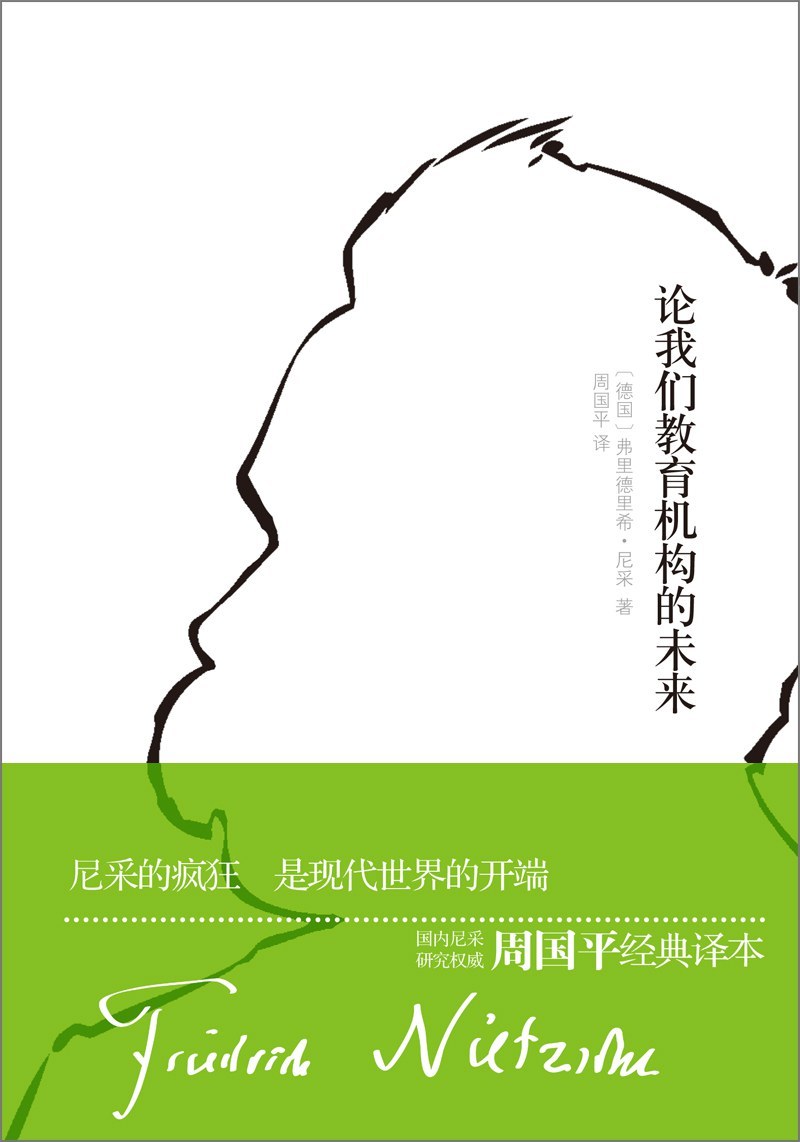
经典文本的语言结构本身就是思维训练的最佳载体。海德格尔在解读荷尔德林诗歌时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经典作品的语言密度与思想深度,要求读者进行持续的智力投入。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论证,需要构建严密的逻辑链条;理解但丁《神曲》的象征体系,必须掌握中世纪的神学宇宙观。这种“费力的阅读”(卡西尔语),如同肌肉锻炼般强化着人类的理性能力,而算法推荐的“轻松阅读”则在削弱这种认知肌肉。2023年哈佛教育学院的实验表明,持续一年经典阅读训练的学生,其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较对照组提升31%。
(三)经典作为人性的镜像与伦理的基石
在技术异化日益加剧的今天,经典文本成为守护人性的最后阵地。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现代社会正将人类降格为“劳动动物”,而经典阅读所构建的“精神生活”,正是对抗这种异化的关键。当我们在《罪与罚》中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挣扎,在《活着》中感受福贵的生命韧性,这些跨越时代的人性书写,让我们在AI绘制的完美数据图景之外,看到真实的生命肌理。
AI可以生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准则,却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苦难的救赎”;AI可以计算最优的行为策略,却无法体会《庄子》“庖丁解牛”中蕴含的自由境界。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正是防止人类被技术同质化的精神抗体。
经典文本更是伦理价值的永恒源泉。当算法试图用功利主义计算“最大幸福”,《孟子》的“恻隐之心”提醒我们,道德的本质是人性的觉醒;当AI伦理陷入程序正义的困境,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规则的伦理路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无知之幕”的构想,本质上是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洞穴隐喻”的现代转译;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对话术的精神传统。这些经典中蕴含的价值体系,如同古希腊的“阿瑞忒”(卓越)追求,为技术发展划定了伦理边界——它们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的精神丰富性为代价。
(一)时间伦理:对抗即时性的精神修行
面对AGI带来的认知挑战,我们需要重构阅读的三重伦理。首先是时间伦理,拒绝算法制造的“即时满足”,重拾本雅明所说的“缓慢阅读”。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三十页篇幅描写玛德琳蛋糕的味觉记忆,这种“凝视式阅读”教会我们在信息洪流中驻足沉思。在数字时代,这种慢阅读具有对抗时间碎片化的救赎意义——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今天转化为对阅读节奏的主动掌控。神经科学家发现,深度阅读时大脑会产生α波,这种脑电活动与冥想状态相似,能够促进深度思考与创造力的迸发。
经典阅读的时间伦理还体现在“重读”的价值上。卡尔维诺指出,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这种循环往复的阅读过程,构成了精神成长的螺旋上升。阅读《论语》,少年时感受道德教诲,中年时领悟处世智慧,老年时体会生命圆融,每个阶段的重读都是一次自我认知的更新。这种时间维度上的意义生成,与算法推荐的“一次性消费”阅读形成鲜明对比——当我们在电子书上标注的笔记随着云端同步消失,经典文本的纸质书页上却沉淀着不同时期的阅读痕迹,成为个人精神成长的年轮。

(二)对话伦理:构建跨时空的思想共同体
其次是对话伦理,打破算法构建的“回声室效应”,建立跨时空的思想共同体。当我们阅读《理想国》时,不仅是与柏拉图对话,更是加入了从阿奎那到罗尔斯的千年哲学辩论;研读《诗经》时,聆听的是从孔子到叶嘉莹的诗教传统。这种超越时空的思想共振,正如怀特海所言“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注脚”,经典文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互文网络”,让我们在技术打造的信息孤岛中重建精神连接。在敦煌文献的残卷中,我们看到唐代僧人对《金刚经》的批注,这种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证明经典阅读本质上是加入一个永不落幕的精神盛宴。
对话伦理还要求我们在阅读中保持批判性思维。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应成为经典阅读的基本态度——我们既要倾听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也要反思其理想国设计的局限性;既要感受杜甫的沉郁顿挫,也要审视其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这种“同情的理解与批判的超越”(伽达默尔语),使经典阅读成为激活思想创造力的源泉。当AI生成的文本试图模仿经典的风格,真正的经典阅读却在教会我们辨别:机器可以复制语言形式,却无法拥有但丁穿越地狱时的精神震颤,无法体会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生命重量。
(三)价值伦理:守护人类文明的精神灯塔
最后是价值伦理,警惕技术理性对人文价值的消解,守护经典中的永恒命题。当AI开始计算“幸福指数”的最优解,《庄子》对“至乐无乐”的追问让我们反思科技主义的局限——幸福不是数据模型中的最大值,而是心灵在超越功利后的自由舒展;当算法试图量化“正义”的标准,《论法的精神》对权力制衡的论述提醒我们法律背后的人文底色——正义不仅是程序的正确,更是对人类尊严的终极守护。这些经典中蕴含的价值体系,为技术发展划定了伦理边界。
在教育领域,价值伦理的重建尤为迫切。2024年教育部调研显示,某省高中课本中现代网文占比已超过经典文学作品。这种“去经典化”倾向正在切断年轻一代与文明传统的精神脐带。大学通识教育中,经典阅读课程的边缘化导致学生陷入“专业深井”,缺乏应对复杂时代问题的人文视野。正如白璧德在《人文主义与美国》中警示的,放弃经典阅读意味着放弃人类文明的精神根基,最终将导致“技术人”的片面发展。
(一)数字时代的经典呈现方式创新
面对AGI技术,经典阅读的传承需要创造性转化而非被动防御。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文物库”将《千里江山图》转化为可交互的3D模型,使观众在滑动屏幕中感受青绿山水的笔墨精神;哈佛经典阅读计划开发的AI导读系统,通过语义分析帮助读者理解《利维坦》的复杂论证结构。这些技术应用不是对经典的消解,而是拓展了经典与当代人对话的渠道。关键在于保持技术工具的从属性——正如竹简、活字印刷、电子书只是载体演变,经典的精神内核始终需要人类主动的心灵投入。

(二)教育体系中的经典阅读重构
学校教育应成为经典阅读的主战场。芬兰在2023年推出的“新基础教育大纲”中,将经典文本阅读纳入核心素养,要求中学生每年精读至少10部跨文明经典。这种教育改革的背后,是对“培养完整的人”的坚持。在大学层面,芝加哥大学的“经典著作阅读计划”持续百年,证明通识教育中经典阅读对培育批判性思维和价值判断的不可替代性。教育者需要意识到,当AI能够完成知识的存储与检索,人类教育的重心应转向不可计算的精神能力——如共情、审美、道德判断,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深深植根于经典阅读的土壤。
(三)在技术辉光中守护人性的火种
在雅典学院的遗址上,镌刻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诫命;在AGI时代的精神入口处,或许应该写上“不读经典者难以自持”。当技术如同普罗米修斯的火焰照亮世界,经典阅读就是那片能让火焰温暖而不灼烧的橄榄枝。它教会我们在算法编织的虚拟花园中,培育真实的精神根系;在AI生成的完美文本之外,守护人类独有的阅读痛苦与思想尊严。正如博尔赫斯在图书馆隐喻中揭示的:经典不是尘封的古籍,而是人类在每个时代重新发现自我的镜子。当我们翻开《尚书》的“克明俊德”,重读《神曲》的“地狱篇”,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终将在AGI的辉光中,照亮人类走向未来的精神之路。
站在人类文明的新起点上,经典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知识获取,成为一种保持精神独立性的生存策略。它让我们在技术构建的“第二自然”中,始终记得自己首先是“会思考的芦苇”。
AGI时代重读经典的终极意义应是——在技术洪流中锚定人性的坐标,让人类文明在创新与传承的张力中,走向更具尊严的未来。当机器学会了模仿人类的语言,我们更需要用经典来确证:人类的独特性,存在于对永恒价值的不懈追寻,存在于与伟大心灵的跨时空对话,存在于每个深夜翻开泛黄书页时,那一丝照亮精神世界的微光。
作者简介:
徐飞博士,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哈佛大学、MIT高级访问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
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CAMEA)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学会组织与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创新创业创造50人论坛主席,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会长。

1本文为《每日经济新闻》原创作品。
2 未经《每日经济新闻》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等,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