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走过隆里城内的青石板路,掬一捧古井水饮下,看天边晨光熹微。这般宁静不会长久了,一番暴风骤雨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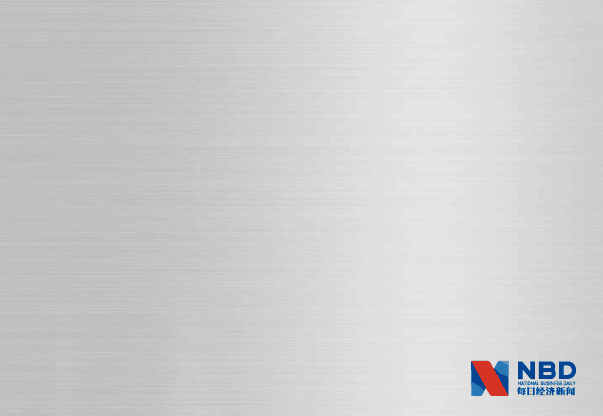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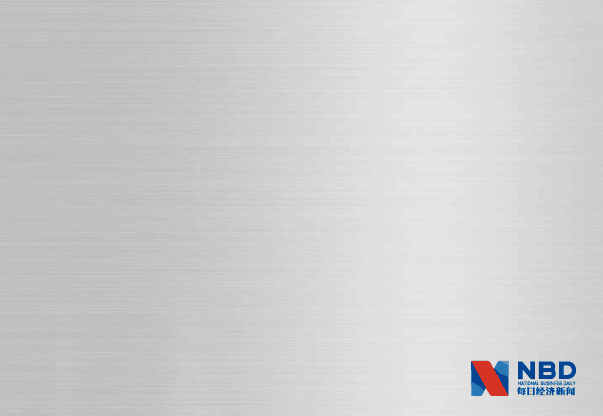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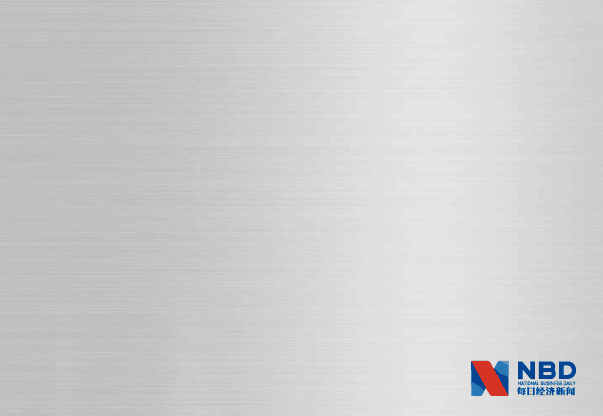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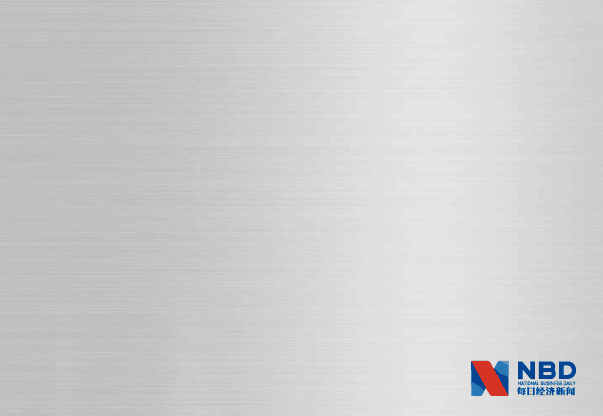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隆里古城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茫茫林海中,是一片开阔的山间盆地,群山环抱,阡陌纵横。它是明朝遗存的军事城堡,城内居住着明代镇压苗王的军人后裔。时光走过了六百年,它亘古如斯。
可就在宁静的表象之下,却处处暗流汹涌。几近破裂的宗族关系,严重缺位的乡村教育,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所有这些都让这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时光的漫溯中渐渐迷失了方向。她的儿女们不再把她当做念兹在兹的人生皈依,也不愿回味她所承载过的温暖记忆,他们急切地去闯荡外面的世界,企图找到另一个精神家园。
于是,乡村慢慢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内核,遗落了农耕文明积淀下来的全部成果,失落地埋下了头。
宗族关系:渐行渐远家族情
古城里的仅存的几座祠堂,终年紧锁大门,四周高墙已经斑驳。这些祠堂,见证了古城六百年的变迁,岁月流转在它们身上留下了关于家族历史、宗族文化的全部记忆。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祠堂被拆除,一代代人的童年湮没在这片片青瓦中,以此为象征的宗族情谊也日渐淡漠,那曾经让所有族人崇敬的信仰正渐行渐远。
祠堂的门环早已锈迹斑斑,“吱--”的一声,我推开一道门缝看去,院子里杂草丛生,前几日下了雨,地面坑坑洼洼,甚至还有些积水,看来是很久都没人清理打扫了。坐在城门洞口歇息的老人告诉我:“从前族里有人专门负责看守打扫祠堂,现在啊,年轻人都出去了,一年都难得开次门。很多都拆了,集体祭祖都很少了。”隆里古城曾有七十二姓氏,很多姓氏都已消亡,如今只剩三十多个了,靠姓氏维系着的宗族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现代化的浪潮席卷隆里古城的时候,那份曾经对祖先、对宗亲坚定的信念开始动摇。
从建国之初开始和外界通婚开始,一直无声无息繁衍着的人们,思潮就开始备受冲击。从前对大家族的倚靠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小家庭的幸福成为他们最大的关注。当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这些在乡村寻常的事宜都可以被村委会等基层政治机构来处理的时候,曾经的宗族角色便淡化了。而当新农保、低保、农业补贴这些关乎乡民切身经济利益的政策都可以由村民自治组织来完成时,宗族权力更是降到了冰点。
在村民胡延平家的外墙上,我看到一张已经褪色的红纸,上面记载了他儿子结婚时前来道喜的亲戚的名字,只有寥寥十来户。他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至亲,很多关系疏远的都不往来了。”当宗亲不再参加被乡民最看重的红白喜事的时候,宗族关系也就渐行渐远了。
当宗族情谊被法治、金钱这些冷冰冰的词汇取代的时候,乡村的人情味儿便丧失殆尽了。
乡村教育:难以回头的荒漠化
“我再打个电话和我妈商量下吧。”十五岁的玖玖两只手搓着衣角,低着头嗫嚅道。眼前的这个女孩,刚参加完中考,但是没发挥好,只考上了县里的一所普通高中。爸爸妈妈觉得,读个普通高中还不如出去打工,家里还有个弟弟在读书,负担也不轻。可玖玖想读书,她不愿像她两个姐姐一样,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在工厂里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尽,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
眼前的这个女孩和她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她需要说服母亲,才能获得继续上学的机会。当经济浪潮席卷了整个村庄,目光短浅的人们误以为外出打工就是最好的出路。
传说王昌龄曾谪迁此地为官,给后人留下了崇德敬学的品质,六百年间这里出过的进士举人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自家门梁上刻上“书香第”、“科甲第”之类的字眼,以表达对读书人的尊敬。可是,如今“书香第”里每天传出来的只有哗啦啦的麻将声,农闲时村民们嗜赌如命,再也不会有“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的动人场景了。
学校在村东头,因为学生太少初中和小学合并办学了。操场上野草疯长,公告栏里的粉笔字依稀可见,课桌椅陈旧不堪,到处都是颓败的气息。杨老师已经在村里教了十年书,闲谈时她忍不住跟我抱怨:“现在家长急着让孩子出去打工,学生越来越少,今年参加中考的只有三十个了。老师的地位也不比从前了,有时候感觉特别力不从心。”
古城内历史悠久的龙标书院,昔日“小童三唤先生起,日满东窗暖似春”,如今几近毁损,荒草丛生,荷塘干涸。严重缺位的教育,丧失地位的老师,目光短浅的家长,无心上学的孩童,乡村教育正一步步踏入荒漠,六百年来隆里古城汲取的全部养分逐渐流失,让人心痛。
身份认同:故乡在何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过“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人们对故土的情感悄然隐匿,把土地当做束缚自己的根源,他们迫不及待寻找自由,心急火燎地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
村里老人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在东莞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上万遍,在福州的工地上干着一天十多个小时磨大理石的苦工,在苏州的纺织厂里穿着工作服忍受着三十多度的高温。为了抹去乡村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迹,小伙们抽着烟拗一个别扭的造型,姑娘们认真地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他们厌恶“乡村”这个土气的标签,一心远走高飞。
在广州打工数年回到隆里的胡江,替父亲看管着家中的化肥店。“其实挺不想回来的,在外面生活惯了,这边晚上静悄悄的,也没什么活动,以前下了班和工友们一起逛街吃夜宵什么的,现在什么也没了。”和胡江不一样的是,很多人出去之后就再不回来,因为乡村太贫困了,他们想要物质更加丰富的生活。于是,他们出走了,摈弃了乡村精神,遗忘了乡村生活的救赎与信仰,也不愿回想起父辈口耳相传的乡村故事。
那晚古城停电,我和村里的大学生泽磊坐在石凳上聊天,他明年就要从贵州师大中文系毕业。他告诉我,“最好能留在贵阳当个语文老师呗,这地方环境好空气清新,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不想回来。”月亮明晃晃,虫虫儿在远处鸣叫,我们不言语,任清风从耳边拂过,乡愁越飘越远。
隆里旅游开发已经在规划之中,一部分村民响应号召已经在城外建房了,这里宁静的乡村生活不久之后将被打破。村民们虽然对目前生活秩序被干扰颇有些微辞,却也盼望着游客到来,收入能再多一些。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颓败的气息,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诗意正在消失殆尽。
清晨,我走过隆里城内的青石板路,掬一捧古井水饮下,看天边晨光熹微。这般宁静不会长久了,一番暴风骤雨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
日暮乡关何处是,在乡村礼数和历史传统被统统破坏之后,乡村终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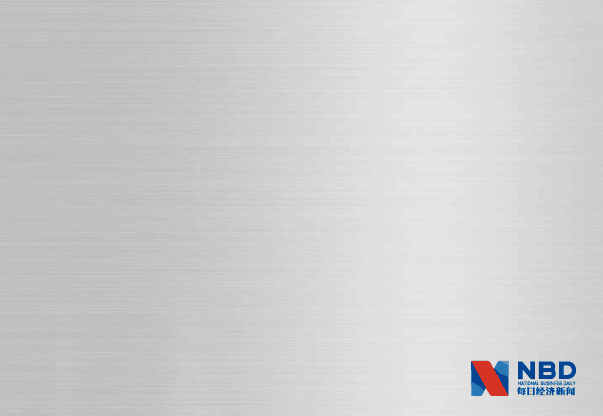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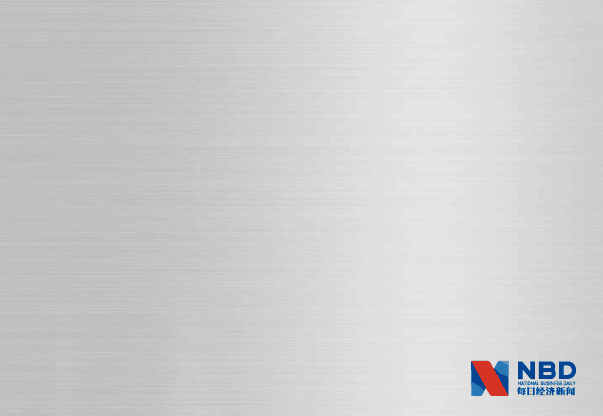 林东岳
林东岳

